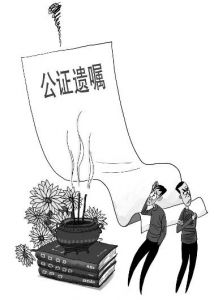
又是一年清明將至。在涉及身后事的話題中,遺囑總是一個很難繞過的部分。立不立遺囑,一份遺囑也許只是寥寥數語,卻不僅是經濟問題、法律問題,背后更蘊含著對遺囑人意志的一種表達。
網絡遺囑向移動端迭代
持續服務等問題存爭議
未表達的情感,未實現的心愿,未告知家人的財產信息……將“身后話”和“身后事”隨時隨地書寫和交代,將生前重要的數據信息保管起來,等故去后再傳遞給至親好友--這并非是情感電影里的橋段,而是互聯網上一些提供遺囑、預囑服務平臺的功能介紹。
最近有互聯網公司推出了這樣一款移動應用:用戶可留下音頻、視頻、文字、圖片等媒介信息,分裝在不同盒子里,每個盒子指定一位接收人,并設定激活機制如:定時發送、失聯后發送、死亡后發送及是否預先告知等。華商報記者聯系該公司了解到,除了免費贈送的激活資格,每個盒子收費每年68元,按使用年限計算。
其實,網絡遺囑在幾年前就出現了。四年前馬航MH370事件發生時,一家經營網絡遺囑的網站曾引起輿論關注。這家網站推出收費的在線遺囑保管箱,幫助用戶備份遺囑、財產、債權等文件掃描件,銀行賬號、保險單號、游戲賬號等信息,遺愿清單甚至私密存檔等,并將遺囑內容指定一個或數個聯系人,以備不時之需。
雖然網絡遺囑保管從PC端迭代至移動端,一些基礎服務并沒有發生轉變。就拿突然身故來說,這些平臺基本都是按用戶預先設置的登陸頻率來予以識別,假如用戶未能定期登陸,平臺會通過郵件、短信直至電話等手段來聯系和委婉確認。
面對新穎卻又略帶忌諱的網絡遺囑,外界反應可謂大相徑庭。支持的聲音中,大多認為這是寄托情感、為人解難的新工具,了卻逝者心愿,給家人帶去心靈慰藉。不過,也有人對信息安全和持續服務等方面提出疑問。
在某公號一篇介紹網絡遺囑的文末,就有用戶評論稱:“如果網站被黑客攻擊了,銀行賬戶會被泄露嗎?也有用戶提出:”我今年20歲,能撐到我需要交代后事那天嗎?“還有用戶自稱:”曾經我立了一個網絡遺囑,后來沒續費,于是就過期了。"
網上立遺囑界定有難度,公證遺囑效力最強
遺囑是對遺產或其他事務所做的個人處分,屬于單方法律行為。那么,在網上寫下的遺囑是否具備法律效力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我國遺囑的形式有5種: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口頭遺囑、公證遺囑。
“從網絡遺囑的內容看,不少是把自書、代書、錄音、口頭等遺囑上傳至網絡保存。”陜西永嘉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姬英凡介紹,繼承法要求,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標明年、月、日等;錄音、代書以及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
姬英凡說,從過往法院判例來看,判斷遺囑是否有效的關鍵在于,立遺囑的人是否出于真實的意愿作出。拿最常見的自書遺囑來說,也就是某人過世前自己親筆寫下的遺愿內容,沒有特殊相反的證據,一般會認定有效。但要界定網絡遺囑是否確屬本人意愿有難度。
陜西涇渭律師事務所李德軍律師表示,網上立遺囑是有法律效力的,但這是在不出現爭議的情況下。如果繼承人提出異議,要證明是誰在電腦旁敲下的遺愿內容也不容易。
那么,比較保險的立遺囑方式是什么?兩位律師都推薦公證遺囑。即便不做遺囑公證,起碼是在繼承人和權利人都知情的前提下,協商后將遺囑內容寫清楚。
李德軍表示,雖然5種遺囑形式都是具備法律效力的,但是從法律效力的高低程度來看,公證遺囑是最高的。因為,這種遺囑有了第三方、具備權威效力的機構為內容進行了見證,一旦發生糾紛,公證遺囑也最為真實有效,最難以被推翻。
提供遺囑保管的機構漸多,西安立遺囑人群年輕化
近日,已經發布了近五年“遺囑白皮書”的中華遺囑庫進入公眾視野。作為提供遺囑第三方保管的公益組織,其在北京掛牌運行,并在天津、廣東、江蘇等地設立分庫。華商報記者致電中華遺囑庫了解到,目前在陜西暫時還沒有網點,但接受跨省遺囑保管辦理。
有行業人士介紹,國內提供遺囑保管的除了一些網絡公司,實體組織則有公益基金會和各省市公證處,像中華遺囑庫就屬于前者。華商報記者了解到,陜西省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會也提供遺囑寄托服務,此外公證部門也承擔這項法定業務。
由于提供遺囑保管的機構諸多,總數難有統計,這意味著,國內遺囑具體訂立量不詳。
各類遺囑中法律效力最高的公證遺囑,目前由全國各地的公證單位辦理,數量也相對可查。記者從西安司法部門了解到,最近幾年,西安每年辦理遺囑公證的數量平均在200多件,大致和其他一些省會城市相當。
據西安市公證處副主任夏秀武介紹,近年來辦理公證遺囑的人群,出現年輕化趨勢。他表示,一般立遺囑的以70-80歲的老人居多,但也有30、40歲就立遺囑的人。可以說,中青年辦遺囑公證已不算是稀奇事。
夏秀武說,其實立遺囑人群年輕化不難理解:不少家庭財富快速積累,一些企業負責人防患遺產紛爭;其次是過去人們普遍忌諱立遺囑,隨著文化認識的轉變,立遺囑多了、時間也提前了;另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常年外出防患于未然,或者身患疾病。
從遺囑內容來看,西安地區的公證遺囑大多涉及房產、股權和存款分配。記者還從陜西多家律師事務所了解到,房產是遺囑處置中最常見的財產類型,這與中華遺囑庫公布的全國數據也比較吻合:因為房產價值的上漲,導致房產成為個人主要財產之一。在該庫登記遺囑中,處理房產的比例占到99.69%。
除了傳統觀念制約
產權等因素也影響遺囑訂立
在國內,遺囑訂立比例仍然偏低。有消息稱,目前我國成年人訂立遺囑比例約在千分之一,西方發達國家立遺囑的比例在八成以上。
與人口自然變動對比,西安每年幾百件的公證遺囑也不多。《2017西安統計年鑒》顯示,2014-2016年,全市人口增長呈高出生低死亡,出生人數分別為8.7萬、8.8萬和10.12萬人,死亡人數為4.71、4.78和4.74萬人,這樣算下來,辦理遺囑公證的不足1%。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石英分析,遺囑普及度不高,一方面和傳統文化影響有關,許多家庭沒有立遺囑的觀念和需求,“在傳統觀念里,子承父業,就像父債子還一樣天經地義。這是過去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家庭結構所決定的。一家人住的是祖宅,是家族共有資產,不是個人的,吃飯在一起,勞動在一起,財產是共同勞動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和過去私產不足有關,由于社會財富的不斷再分配,不少人覺得無財產可立。
按照中國人傳統,子女對父母的財產存在天然期待。這種期待被打破,就可能是引爆爭吵之時。據臺灣媒體報道,知名作家李敖3月18日辭世,長女李文隨后就發布聲明,要求看遺囑并表示會打親子關系的訴訟爭取認祖歸宗。
曾接觸過多起遺產糾紛的姬英凡說,因為遺產分配而導致母子、兄弟對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鮮見。而這背后,實際上是各方對財產分配份額的質疑,“子女往往覺得,父母的應該就是我的。有兄弟姐妹的,大家想當然覺得就應該平分,甚至遺囑本身也可能成為爭議的焦點。”
夏秀武表示,除了傳統觀念和習俗制約,遺囑能否順利訂立還需要考慮所分配財產產權、遺囑人條件等現實因素。他說,遺囑公證要遵從訂立者意愿,遺囑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簡單說就是意識清楚、表達清晰,不糊涂。同時,遺囑分配需要考慮權利褫奪因素。另外,遺囑分配中常見的不動產財產,需要先明確相關產權權利,例如:產權不明的公有產權房、子女或他人出資購買等因素,也可能影響遺囑的訂立。
對遺囑共識是法治社會的轉變
這個過程可能不會太長
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在老齡化日益加劇的今天,作為財富傳承工具的遺囑正日益被重視。李德軍表示:“在目前法院審理的遺產糾紛中,有大量因為沒有遺囑或者遺囑不符合《繼承法》規定的形式要件而無效,導致繼承難問題。所以,訂立符合法律要求的遺囑,可以更好的避免家庭糾紛的發生,也可以利用遺囑的方式完成更簡便的繼承手續。”
石英認為,傳統聚居和共同生活的經濟基礎正在逐漸消失。隨著家庭小型化和資產登記的日益完善,特別是家庭可分配財產的增加,父母的財產中,子女的貢獻部分已經很少。
“經濟獨立了,也就意味著老人更有了自主處理財產的底氣。”石英表示,其實對于遺囑認識的轉變,也反映出我國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并不會很漫長。正如英國法學家梅因在《古代法》一書中所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相對于舊有的財產分配觀念,遺囑是一種契約,意味著我們是獨立的個體,我的財產可以由我來做主決定。
本地民俗文化專家王智表示,過去遺囑訂立比例不高,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和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有關,對于遺產繼承,很多人會覺得沒有立遺囑的必要。未來隨著我國家庭組成結構逐漸變化,對于遺囑的需求也會增加。
有法律專家表示,從長遠來看,減少財產繼承糾紛,既需要公眾轉變觀念,正確認識遺囑的訂立,而政府和其他社會角色也不應旁觀。他說,除了效力最高的公證遺囑,目前國內推動遺囑登記和普及的公益機構也在增加,并制作了遺囑范本和建立了自己的數據庫。但整體來看,這類組織數量仍然偏少,而且缺乏一套完整的標準,如果能給予各類組織更規范的支持,也有助于遺囑普及的工作。 華商報記者 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