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嶺魅力

賈平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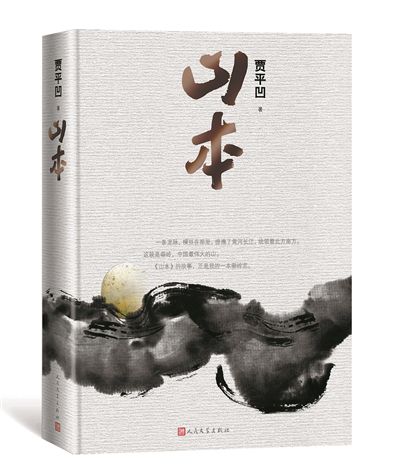
《山本》 賈平凹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日前,作家賈平凹聯手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山本》精裝版,并亮相第47屆倫敦書展,引發國際關注。《山本》是賈平凹的第16部長篇小說,也是他醞釀多年立意為秦嶺做傳、為近代中國勾勒記憶的史詩之著。
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間秘史
按賈平凹自己的說法,“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嶺志”。這是一本以秦嶺為背景的小說。
小說發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秦嶺深處一個名為渦鎮的小鎮為起始,講述了楊家棺材鋪童養媳陸菊人從娘家帶來了三分胭脂風水寶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贈予井宗秀葬父后,竟使渦鎮的世道完全改變,從而引發了一幕幕激烈動蕩的戰爭,多股勢力一時間風起云涌,割據各方不斷廝殺,同時井家兄弟之間的特殊關系與阮家族群的刻骨仇恨也在特定的時期與地點中變化升級。
這場紛繁迷亂的歷史大戲中,作家著重凸顯了陸菊人的善良、盲人郎中陳先生的通達、地藏菩薩廟里寬展師父的慈悲,這些善意與超脫,為整部作品溫暖了底色。
據悉,賈平凹原意是寫一部秦嶺的散文體草木記、動物記,在走訪中,卻不由得寫成了一部宏闊而具有藝術內蘊的歷史小說。《山本》描述的是約100年前的秦嶺地區的社會生態,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里,作家以獨到的體察和歷史觀,表現了底層民眾的生命苦難,寄寓著作家真切的悲憫情懷。
除此之外,作者更是對秦嶺一代的草木鳥獸有著詳盡的描述,篇幅之多足以稱得上一部秦嶺地方志。
評論家陳思和在讀完這部小說后說:“既有飛禽奔獸,也有魍魎魑魅,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事,都依托了秦嶺這個大背景,絮絮叨叨地顯現本相……《山本》里大量描寫秦嶺博物風情的段落,可以看作是作者創作這部小說的初心所在。《山本》作為秦嶺志的存在,其壽命要比山本各路賢愚的性命要長得多,但是《山本》在秦嶺的存在面前,同樣也是微不足道。這就是來自秦嶺的自然、人事和言說的關系。”他把《山本》作為民間歷史敘事的一部佳作。
一部生命之書 一部悲憫之書
“最初我在寫我所熟悉的生活,寫出的是一個賈平凹,寫到一定程度,重新審視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發現和思考,在謀圖寫作對于社會的意義,對于時代的意義。這樣一來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尋找題材,而似乎是題材在尋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賈平凹,好像成了這個社會的、時代的,是一個集體的意識。”賈平凹說。
賈平凹的第十六部長篇,與眾不同的特點在其亦莊亦諧,大的時代風云下,人之命運的不能自主,暴力沖突的血腥殘酷,令人欲哭無淚。而風暴間歇,女人對美的追求,動物生靈對吉兇禍福的警示,又常常令人莞爾。作者對當下現實生活的見聞體驗,也常常出其不意地換裝現身于彼時彼地,令人有一種抽離小說寫實場景而忽然坐在戲臺下看戲的感覺。另外,對于虛實關系極其巧妙的藝術處理也令人贊嘆。
評論家王春林說道:“作為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山本》不僅有對秦嶺的‘百科全書’式書寫,而且也有對近代中國的深度反思。一方面,對渦鎮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充滿煙火氣的世俗日常生活進行著鮮活表現;另一方面,也有著哲學維度的形而上思考。《山本》,是一部生命之書,一部苦難之書,更是一部悲憫之書。”
新作一出版即亮相倫敦書展
《山本》人物眾多,群像各有面目。小說氣韻飽滿貫徹始終,對于秦嶺山水草木、溝岔村寨的勾畫,對當地風物習俗的描寫,清晰而生動,使讀者如置身其中。記者獲悉,賈平凹新作剛剛在國內預售,就已經被引進參加第47屆倫敦書展,被多家國外出版商看中,并簽約版權轉讓。
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書記張賢明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文化的交流與互鑒是雙向的,希望隨著走出去步伐的不斷加快,越來越多優秀的中國文學能夠真正進入英國讀者的視野。《山本》的簽約,意味著國際出版市場已開始積極跟進中國當代文學的出版動態,使得最新出版的作品能夠最快與國際讀者見面。”
對于最新長篇,賈平凹表示:“《山本》是在2015年開始了構思,那是極其糾結的一年,面對著龐雜混亂的素材,我不知怎樣處理。首先是它的內容,和我在課本里學的,在影視上見的,是那樣不同,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諱。再就是,這些素材如何進入小說,歷史又怎樣成為文學?我想我那時就像一頭獅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鉆進偌大的荊棘藤蔓里,獅子沒辦法,又不忍離開,就趴在那里,氣喘吁吁,鼻臉上盡落些蒼蠅。”如今,這本書終于面市,接受讀者的檢驗。